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建立至今,逐步与反贫困战略形成合力,在保障和实现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理性的制度设计也容易受到“人”的因素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发生目标与效果的偏离。在新时代,应该重新认识低保制度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作用和对整个反贫困行动的意义,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低保标准,适当提升我国城乡低保标准的实际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完善低保制度的治理机制,使其在反贫困行动中发挥更大的实际效果。
低保制度是一项底线型的救助制度,以“底线公平”为根本价值准则。这是低保制度首要的功能定位,也是低保制度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与社会权责关系的基本依据。虽然低保制度应坚持“底线”、“兜底”价值取向,但并不意味着低保应该维持较低的保障水平。我国现行低保标准虽然完全能满足维持温饱的需要,但无法满足贫困者共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在最大限度实现“底线公平”、强化低保保障作用不断提升的同时,也要防止受助对象产生“福利依赖”。因此,需从多维度对低保制度进行治理机制创设与调整。
第一,提高农村低保金补助水平,增强最贫困群体的扶持程度。在全国农村地区建立和完善农村低保金与物价增长联动机制,使低保金增速与物价增速至少保持一致,保障农村贫困群体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实行低保金增速高于物价增速的机制,使贫困群体的购买力相对物价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强对最贫困群体的扶持程度,可将贫困群体分为极端贫困、严重贫困、中等贫困和接近贫困四个层次,建立梯度化的补助指数,贫困程度越高的家庭获得越多的补助金,保障其收入增长幅度越高,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和质量。
第二,完善低保对象的识别和认定方法。目前,还存在对低保对象识别不准确,差额发放执行不到位的现象,导致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相对贫富关系因低保补助而发生改变,尤其是改变了那些收入水平接近但又分别位于低保线上下的家庭的相对贫富关系,形成了新的水平差别。伴随着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和家庭收入的多元化,非正规就业和隐性收入增加了城乡低保对象的识别难度。为了解决识别困境,一方面,应在家庭经济状况调査中,综合使用个人申报法、入户调查法、邻里走访法、信函求证法、部门联动法、跟踪了解法以及居民代表评议法等,以客观、全面地对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完善城乡低保公示制度,保证公示内容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的动态信息。
第三,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建设。低保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县、乡镇)层面,特别是低保对象的认定、审核、管理以及低保金发放等关键性活动。因此,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无疑对于政策的最终效果将产生重要影响。基层政府在诸如低保政策落实等工作中以协商者、支持者和平衡者身份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从而调动社会多样化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符合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改革创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适当提供一定资源以增强村干部在乡村社会的工作动力,以尽量避免将低保执行转变成为治理手段;乡镇要加强对村干部进行低保政策性质教育,并采取合适的抽检方式对落实的低保对象进行调查,限制村干部在低保执行中的变通空间。加强低保执行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在制度层面降低产生瞄准偏误的风险。
第四,健全低保与其他制度的衔接机制。加强低保救助与新农保、新农合等社保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同时弱化低保与医疗、教育等其他救助项目的捆绑。目前,由于“泛福利化”现象的存在,专项救助变成了低保户的专项福利,实质上纵容了低保中的非特殊困难群体对公共资源的滥用,是对其他贫困群体应享有的社会保障的剥夺。随着低保重回底线救助,专项救助就需要建立自身独立的制度轨道,包括设立制度化的申请程序、救助标准、救助对象及识别机制。有特殊需求的贫困群体与低保户均可申请,但必须同等地按照专项救助制度流程进行申请,只有符合条件的才能够获得专项救助。将超越底线的救助转轨到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并以制度衔接的形式解决低保户的其他社会需求,真正建立起运转良好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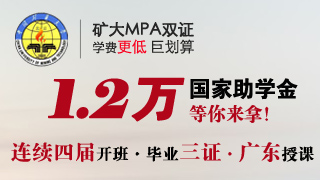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